随机事件

我的舅舅彼得是一名成功的大法官,他是我母亲的弟弟,我的母亲去世以后我们就是彼此唯一的血缘亲戚了,今天他就在我们家里作客,我的妻子玫瑰是个烹饪高手,她做的一桌好菜让彼得赞不绝口,这也是我的骄傲。彼得舅舅一直没有结婚,他能够有今天的成就也付出了艰苦的努力。
我记得小时候彼得舅舅很会讲故事,每次家庭聚会的时候,他会把他在法庭上的经历讲给我们听,那些离奇古怪故事常常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,而现在我的儿子们接替了我的工作,他们正缠着老彼得,要他讲故事来听,这是每次彼得舅舅来访时的保留节目。我也饶有兴趣的坐在旁边看着老头子和两个小孩胡闹。玫瑰端上茶,轻轻呵斥儿子们,叫他们不要妨碍大人聊天。今天彼得舅舅的精神很好,他乐呵呵的把其中一个男孩抱起来放在膝盖上对我说:“加林,我快要退休了,但是我最近却越来越经常的回忆起刚刚进入法院工作时的情景,你说这是不是衰老的象征?”
我点上一只烟,透过朦胧的烟雾看着老彼得渐渐生出皱纹的脸没有说话,我记得他年轻时曾经有婴儿一样粉红的皮肤,黑漆漆的头发,而现在坐在我对面的却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儿,脸上的肌肉完全消瘦了,只剩下一层厚重的皮肤紧紧贴在骨骼上,他虽然至今精神健硕,但是岁月的痕迹毫不留情的刻在脸上,而我自己也成了标准中年人,不老才怪呢,但是我相信,以老彼得的智慧他根本不需要任何虚伪的安慰,所以我一直保持了沉默,任由两个小孩子去叨扰他。
彼得舅舅仿佛听到了我心里的话,所以并没有追问我,要我回答问题,而是接着说:“你们想要听我讲故事,我就讲一个我刚刚从法学院毕业,遇到的第一个案子吧。那时候我还是大法官的助理,说白了做的就是替大法官跑腿、整理文件、端茶倒水之类的事,直到有一天我得到一个陪同大法官上庭的机会,当然我去了也只是坐在旁边做做记录,不过这样难得的机会已经让当时二十出头的我兴奋异常了。”
玫瑰收拾完了厨房,也出来加入我们的谈话中,她在我旁边坐下兴奋的问:“你能在法庭上一眼看出谁是罪犯,谁是无辜的吗?我听说法官大都有这样的直觉”,很显然,玫瑰有点浪漫情怀,她流露出一脸钦慕的神情。
彼得舅舅哈哈大笑起来:“我真希望我能有这种直觉,可爱的玫瑰,但愿我能够如此。”
我一边拍拍玫瑰的手背,叫她不要这样大惊小怪的,一边对老彼得说:“作为执法人员你一定很自豪,能够用公正的原则去处理世界上的一切事务。”
“公正吗?不一定呢,你们知道的,法律只是人世间的人们自己为自己订立的规章制度,我们只能做到尽量公正,但是,谁知道呢,我们也只是普通人,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完全公平合理。
“我第一次参加庭询的案子几乎一清二楚,被告人被发现的时候就站在尸体旁边,现场没有人相信站在被告席上的那个人有一丝一毫脱罪的机会,而就是这个案子给我敲响了洪钟大闾般的警告。”
我惊讶的问:“怎么回事?难道他逃脱了罪罚?”
“不完全是”,彼得舅舅看看我们,神情有些怪异。
“什么叫'不完全是'?”,我越来越感到奇怪。
彼得舅舅端起茶几上的杯子慢慢抿了一口茶,看得出来,他的思绪已经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日子:“那个人,那个被告,是个粗壮的大块头,满脸横肉,鼻子因为酗酒而潮红,眼皮上的赘肉使他的眼睛几乎不能睁开,是的,就是这样一个丑陋的人站在被告席上,而且证据确凿,有一名证人,就是被害人的邻居,玛歌太太,她指认出这名被告就是当天晚上自己亲眼看到的人,我记得她当时的证词是这样的:
我一直睡觉容易被惊醒,只要是有一点点声响都会把我吵醒,我睡着的时候,哪怕是街上有人聊天都会让我醒过来。那天晚上,我被一个闷声闷气的、扑倒在地的声音惊醒了,我好奇的站起来走到窗口往外看,我看见康妮太太倒在血泊里,她旁边站了一个人,手里拿着一把匕首,在月光下寒光闪闪,那天夜里月亮很明亮,你们都能查出来的,我还看见那个人胸前溅着一滩鲜血,他听到我开窗的声音,大概出于本能吧,他顺着声响扭过头、向我窗口的方向看过来,正好这时有一辆小汽车拐了个弯,车灯照在他的脸上,使我看得清清楚楚,就是他,就是那个人。
检察官问玛歌太太:你能在庭上指出那个人吗?
玛歌太太指着被告,非常肯定的说:是的,就是他。
而接下来,玛歌太太所说的、开着小汽车的人、也就是高克先生,他也证实了玛歌太太的话。那天晚上他确实驾车回家,路上正好看见被告,他所描绘的情景跟玛歌太太所说的完全一样,而且那个人在他的车灯照耀下惊恐的表情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,他确定那个人就是今天庭上的被告。
这名大壮汉简直就像是在众目睽睽之中捅了别人一刀。
没有任何疑问了,你们一定会说,杀人偿命吧。检察官也是这样陈述的:我认为毫无疑问,正是被告杀死了康妮太太,有如此明确的人证,指纹和血迹都吻合,在此我希望能够给予被告严厉的处罚,不能让他逃脱了法律的制裁。
检察官因为证据确凿而信心满满。
当时我一边埋着头努力的在堆积如山的档案文件纸上记录庭审经过,一边尽可能的动用我的脑袋去思考整个审讯过程,以我当时的学习经历来看,这是大法官让我接受的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案例,我体会到了他的用心良苦,学习的过程都要从简到难,一步一个脚印慢慢的来,这个案子就是这么容易。
这时辩方律师出庭了,我在做记录的空隙抬头看了一眼陪审团席位,陪审员们都已经轻松自如的坐在椅子上,辩方律师的出现几乎只是完成一个法律程序,完全失去了实际的意义。”
我六岁的大儿子正好处于人生的第一个叛逆期,他兴致勃勃的问老彼得:“律师说什么了?他替被告脱罪了吗?”
四岁的小儿子正在老彼得的膝盖上坐着,此时伸出小手轻轻抓住他的白头发玩,我和玫瑰听得津津有味,都想到没有去制止小家伙的无礼行为。
彼得舅舅定了定神,这些回忆显然使他消耗了大量的精力:
“辩方律师开始盘诘证人,他所问的问题并没有超出我在法学院里学到的知识,你们知道的,当年我是以一等优秀成绩毕业的,因此才得到了大法官助理这样一个有着显豁前途的职务。”彼得舅舅有些自豪的挺了挺胸口,微微笑起来,但是他的笑容并没有持续多久,他接着讲下去:
“律师问玛歌太太:夫人,请允许我提醒你,你的证词将决定一个人有罪或是无罪,他是否需要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都取决于你接下来的回答。
玛歌太太点点头:是的,先生。
律师说:你确定你所看见的人就是我的当事人,现在正站在被告席上的那一位吗?
玛歌太太:我确定是他。
律师:你能保证你看清楚了吗?你的视力正常吗?
玛歌太太:我不需要戴眼镜就能看清楚所有的人。
律师:在晚上也一样能看到吗?从你的窗口一直看到街上?
玛歌太太:是的,当时的月光很好,而且还有车灯的照耀,所以我看得很清楚。我的窗口离街面很近。
陪审团成员开始松散了,他们大概和我一样觉得律师有点无聊,而我更是因为猜透了律师的小把戏而暗暗好笑,我真想站起来让这名律师饶了这位太太,她看起来并不年轻了。
律师:你一点都不怀疑你所看见的就是被告吗?
玛歌太太:我再说一次,我确定是他。
律师:你不介意再看一眼那天夜里你所看见的那个人吧。
鬼使神差的,在辩方律师的指挥下,从观众席里走出一个人,那个人居然长得跟被告一模一样,他们是双胞胎!
庭上一片骚动。
律师:现在,玛歌太太,你还能确定你看见的就是被告吗?
玛歌太太不能,她看看这个,又看看那个,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整个法庭一片喧哗。
我就不仔细讲接下来的枯燥的法律程序了,总之,因为证人的犹豫、证据不足等原因,原先几乎是板上钉钉的被告被宣布无罪,两个双胞胎走上前拥抱了一下。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杀人,或者他们中的一个是否杀了人?是站在被告席上的那个,还是刚刚出现的这个是杀人凶手?我连这也没有把握,这是我的特殊日子,也标志着我的职业生涯的非常开端。
如果你问我,法律是否公正,或者再扩大一点范围,人世间是否存在公正,我只能说在一切现世的人为中,我们都没有权力掌握公正,所以不管是执法者还是普通人,都不能信誓旦旦的保证自己公正无私。
当我们走出法庭的时候,包括所有的证人和那对双胞胎一出现,法庭外一群早已得知消息的记者和群众一拥而上,他们冲上来围住我们,这引起了庭外难以平息的骚动与喧哗。法警打算带这两个双胞胎退回庭内,从偏门悄悄离开的,双胞胎中的一个,我不知道是哪一个,说:我们被无罪释放了,不是吗?为什么还要逃跑呢?这是我们出名的好机会。他们大大咧咧的从法院大门走出去,在人群的推攘中微笑、挥手,人群涌动,涌动到大街的中间,双胞胎的其中一个,不知怎么回事,被推了一辆正驶过来的公共汽车的正前方,他像一只兔子似的尖叫、弹起来、掉在地上,我亲眼看见他死去。双胞胎中的另一个冲上去抱住血肉模糊的尸体,悲愤得咬牙切齿,他抬起头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前方,我正好站在他的视线之内。
天谴!
我这样想的,但是我还是不知道受到惩罚的是不是凶手,在一切玄机中没有什么是我知道的,除却人间的公正之外的公正,我并没有能力去揭示。
这样的开端让我小心谨慎了一辈子,我从来不敢保证自己肯定正确,即使我掌握着确凿的证据,即使我把法律条文背的滚瓜烂熟,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正确,作为一个人,我的能力是有限的,能有机会得到这样的认识也算是我的幸运吧,它提醒我,在作出任何评判之前,可一定要小心啊!”
彼得舅舅讲完了他的故事,我们都很长时间没有说话,玫瑰低着头轻轻搓自己的手,两个小孩也规矩了,不再吵吵闹闹。我想今后我们的生活也许会轻松自如一点吧,在判断正误的时候没有人再那么自信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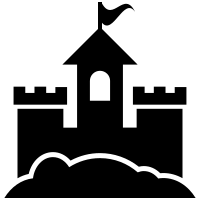 彼得的城堡
彼得的城堡
留言规则:
1、遵守国家法律,请不要发布违反国家法律的内容;
2、遵守社会公德,请不要使用不文明字词作为个人昵称,发布消息攻击、谩骂他人;
3、请不要发送信息垃圾,不要在短时间内反复发布同一条消息;不要发布、传播谣言;
4、新发布留言在15分钟之内可以编辑、删除,经管理员审核后才会正式发布;